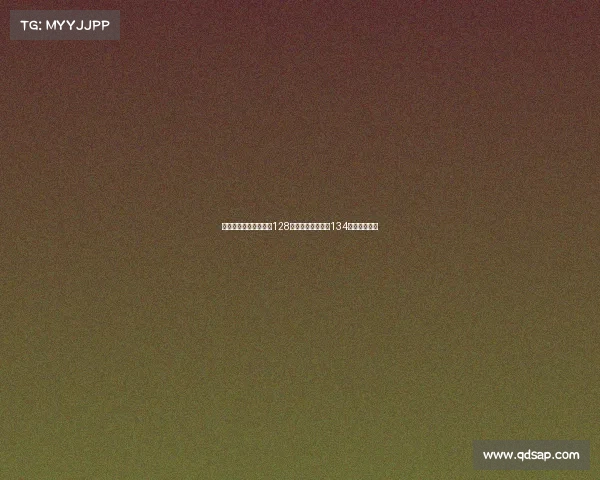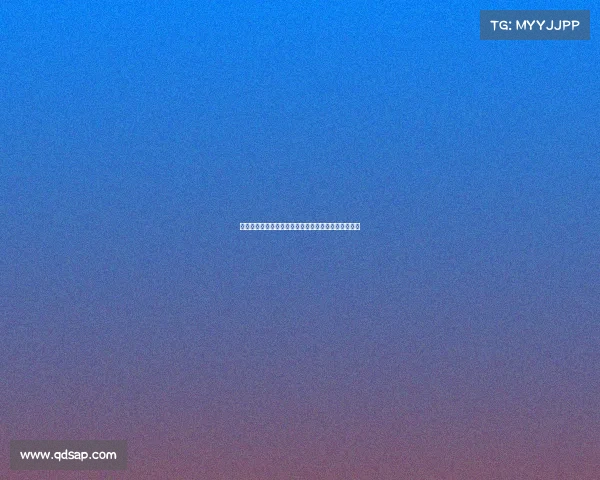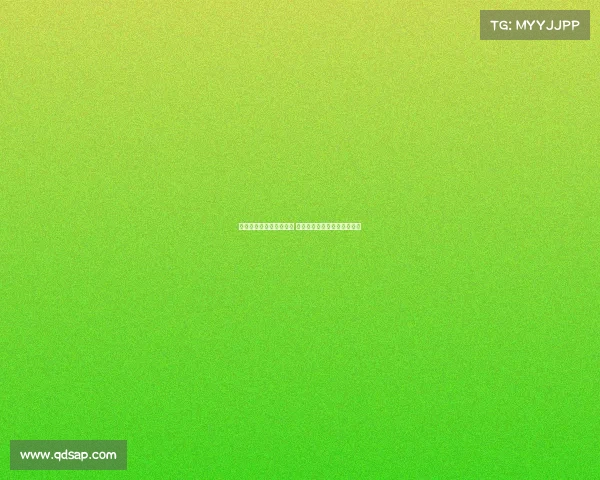文章摘要:本文首先概括了《entity["periodical", "中华遗产", 0]》杂志更名事宜、休刊状态及编辑部所宣布的新方向,梳理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深远意义。文章接着从“更名与主办变更”“休刊与不复刊声明”“文化传承定位变化”“新方向与未来形态”四个维度进行深入阐述,详尽剖析杂志从创刊以来的发展轨迹、停刊原因、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反思、以及编辑部透露的新战略部署。通过对更名背后的出版制度语境、休刊所释放的行业信号、文化遗产期刊生态的挑战与机遇,以及面向未来的新平台形态的展望,本文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解路径:一方面是《中华遗产》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的终章,另一方面是其转型为更广泛媒介形态的开启。结尾处将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指出这一事件既是书籍期刊时代的一个符号性转折,也可能成为文化传播形式更新与再出发的契机。
1、更名与主办变更
《中华遗产》杂志在2025年10月15日正式更名为《entity["periodical", "出版传媒研究", 0]》,这一更名动作不仅是一纸名称上的变化,更意味着其主办单位、出版单位发生了重要变更。citeturn0search2turn0search3turn0search0
根据公开批复显示,原杂志由entity["organization",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0]主办,而更名后改由entity["organizatio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有限公司", 0]承担主办与出版责任。citeturn0search3 这意味着其出版体系与运作逻辑将全面对接新的机构框架。
从杂志创刊以来其主办变迁亦颇为丰富——创刊于2004年的中华遗产,几易其手,2008年起与entity["periodical", "中国国家地理", 0]合作出版。citeturn0search0turn0search6 这一变动,使此次更名显得既是一个周期终结,也是转型节点。
2、休刊与不复刊声明
《中华遗产》在2024年11月22日由中华书局发布休刊公告,自2025年1月1日起暂停编辑、出版、发行。citeturn0search2 杂志至第230期停止了印刷发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citeturn0search3
雷火编辑部通过官方账号明确称“无任何复刊希望”。例如在其微博回应读者问询时表示:“刊号已收归中华书局,我们无法继续使用”。citeturn0search0 这一声明意味着杂志以现有品牌和刊号形式恢复已成不可能。
这一“不复刊”的表态释放出两重信号:一是对当前纸质杂志生存环境的现实判断,二是向市场与读者宣布品牌将以新形态出现。编辑部话语中透露的是一种转型意图,而不仅是终结。citeturn0search3
3、文化传承定位变化
自2004年创刊以来,《中华遗产》专注于自然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发现等话题,定位“让过去点亮未来,让历史影响今天”。citeturn0search6turn0search0 杂志通过丰富的策划栏目和专题报道,在大众文化领域内起到了桥梁作用。
其内容涵盖“最中国汉字”“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项考古发现”“国宝山西”“国宝陕西”等专题,彰显出对中华文明根基的文化自信建构。citeturn0search0turn0search3 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化遗产传播与大众杂志之间的空白。

然而,在数字化、碎片化阅读时代,依靠传统纸媒传播文化遗产的模式面临挑战。越来越多读者转向网络平台、短视频、社交媒体,传统杂志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在逐步收窄。此背景下,杂志立足的“文化传承”定位也不得不思考适应变革。
编辑部在宣布更名与不复刊的同时也透露:“我们会继续开辟阵地,以新的名称和更多样的形式与大家见面。”citeturn0search0turn0search2 这说明虽然《中华遗产》这一刊名和刊号终结,但其团队并未完全退出,而是面向新的传播路径。
新方向可能包括数字化平台、策展活动、跨媒体合作、IP衍生产品等。考虑到主办单位变更为出版传媒商报社,其资源背景更倾向传媒研究、出版体系、传播平台整合,因此未来形态可能更注重“出版→传媒→研究”的桥梁角色。
此外,新名称《出版传媒研究》本身即体现了由“内容杂志”向“研究与媒体融合平台”的转型。通过构建研究型、传播型、互动型内容机制,该平台有机会成为文化遗产传播的新渠道,也可能承担更广泛的文化传媒功能。
总结:
回顾整个事件,《中华遗产》杂志的更名、休刊、不复刊声明以及新方向的提出,标志着一个文化期刊品牌的终章,同时也暗示其团队面向未来的新起点。从更名与主办单位变更可见其出版机制的深层调整;从休刊与不复刊声明中可读出纸媒时代的艰难与转型决心;从其文化传承定位可感受到时代背景下传统内容面对新的传播生态的挑战;而新的方向则蕴含着文化、传播、研究三方融合的可能。
未来,虽然《中华遗产》这一名字将不再继续,但其所承载的文化使命未必终止。编辑部转型的新平台若能抓住数字化、互动化、跨界化趋势,就有可能在新的语境下续写文化传播的新篇章。无论如何,此次更名与转型是我国文化期刊生态内一次值得深思的节点。